股票配资资讯网 生活即教育:生活儒学的教育现象学——儒家教育哲学的当代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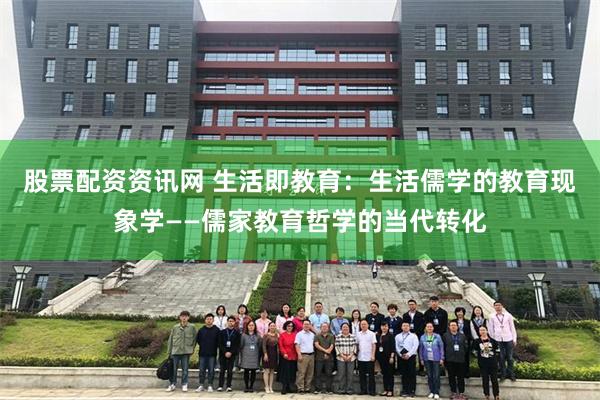

黄玉顺教授
摘要:教育现象学是对教育的现象学反思。依据生活儒学的生活现象学,“生活即教育”。“生活”意指前主体性的“存在”,以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教育活动是一种生活样态,而且从“成人”的教育宗旨来看,作为存在的生活就是教育。所谓“成人”,即“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按照“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首先是生活给出了主体,然后是主体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不论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是“在生活”中生成的教育主体,他们都在“去生活”中发挥其教育主体性。但“在生活”的教育现象乃是“他者教育”,包括受教者方面的受他者的教育和施教者方面的对他者的教育。而“去生活”的教育现象本质上是“自我教育”,这是主体自由意志的选择,意味着“教育自由”;而这种意志自由的实现,则指向“教育权”。教育权的本质是“自我教育权”,即主体“去生活”的自由权利。
汉语“教育”一词,最初见于《孟子》中的“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教育思想从孟子那里才开始。众所周知,教育问题也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贯穿整个儒学史。不过,孔孟的教育思想属于中国“轴心时代”,秦汉以降的儒家教育思想属于中国帝制时代,这是儒家教育哲学的两大历史形态。今天,儒家教育哲学面临着现代转型的问题。为此,本文将探讨当代“生活儒学”视域下的教育现象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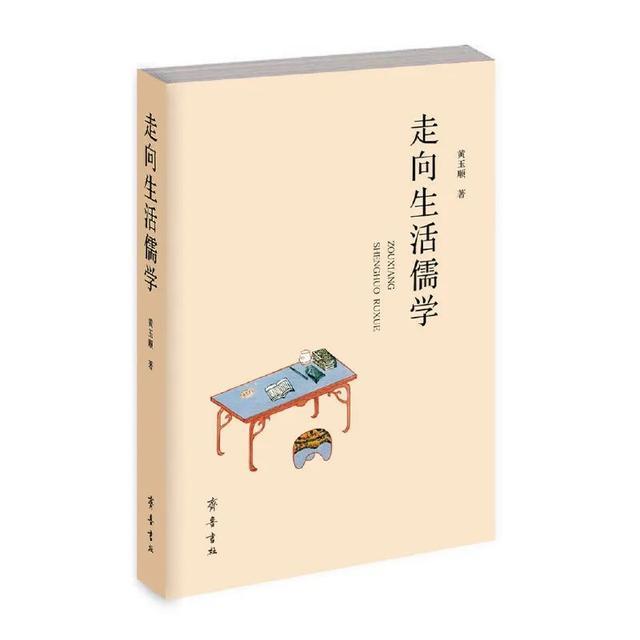
黄玉顺:《走向生活儒学》
一、引论:生活现象学的方法
教育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phenomenon)。但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它究竟是何种意义的“现象”?是“前现象学”(pre-phenomenology)意义的现象,还是“现象学”(phenomenology)意义的现象?这里的分界,就是20世纪胡塞尔(Edmund Husserl)创立现象学而开启世界范围的“现象学运动”。汉语用“现象”翻译西语“phenomenon”,这个汉语词汇出自《易传》“见乃谓之象”(此处“见”读作“现”);《易传》虽然基本上是前现象学的观念,但也蕴含着现象学的意味。
(一)现象学的一般方法
所谓“教育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education),就是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厘清“现象学方法”。胡塞尔之后,现象学逐渐成为哲学以及人文学术乃至社会科学的一种影响深广的一般方法论。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确实,“现象学”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一是在现象学方法统摄之下而形成的“现象学运动”,其中包括复数的诸家“现象学哲学”(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ies);二是单数的现象学方法(approach of phenomenology)本身。对于本文来说,首先应当讨论的是一般的现象学方法。
撇开各种现象学哲学之间的差异,现象学方法一般包括三个步骤:解构→还原→建构。
1.解构(destruction)。从笛卡尔(Rene Descartes)开启“认识论转向”(the epistemological turn)到胡塞尔创立现象学,哲学研究的首要步骤就是解构,即怀疑并暂时搁置一切现存的观念。胡塞尔更彻底地表述了笛卡尔的怀疑论原则:“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性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这就是现象学方法的首要目标:“无前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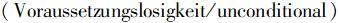
。对于教育现象学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暂时撇开一切既有的教育学和教育哲学的种种成见,即对它们暂时不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儒家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实股票配资资讯网也类似这种“现象学态度”。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当然,本文将会大量引用儒家的论说,但这并非以之为根据,而是首先以教育现象的“事情本身”为根据,然后判定这些论说符合“事情本身”而引用之。同理,本文也会引用既有的教育学和教育哲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2.还原(reduction)。上述“解构”不是简单地否定、抛弃,而是“还原”,即回到并直接面对生活的实情。这就是现象学的口号“面对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t)。当然,究竟何为“事情本身”(Sache selbt/the matter itself),不同的现象学家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胡塞尔认为是先验意识的“意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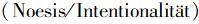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是“此在”(Dasein)的“生存”(Existenz),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现象学哲学。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出自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更接近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但笔者认为,对于教育现象学来说,还原就是通过解构而直接面对教育现象的实情,那么,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更为切近。
这里需要留意“经验”概念,因为海德格尔是要还原到“源始经验”(urspruelich Erfahrung/original experience)“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源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源始经验获得的。”这并非经验主义的“经验”概念,因为经验主义是以“主—客”观念架构为前提,即存在者化的某个主体经验到某个对象。诚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所说,这样的“完全的还原是不可能的”,因为现象学的还原“不是对直接经验的回归,因为我们无法回归到直接经验”。与此不同,海德格尔的“源始经验”则是“此在的生存”。
儒家的“反”(返)的观念接近于“还原”的观念。例如孟子的思想,就类似于胡塞尔的“先验还原”(transzendentale Reduktion)。面对外物,他主张“自返”即“反求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爱人不亲,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自反而仁矣”。这就是说,这种“自返”是返回到“仁”。此“仁”被视为本体,所以叫作“返本”,“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这个本体之“仁”又叫作“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显然,这个“诚”“仁”本体乃是先验的,与胡塞尔一致。不过,孟子之“仁”还有更加本源的意义,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这种作为“始端”的“恻隐之心”,乃是本真的情感(即朱熹所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这就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还原”了,海氏的“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也是情感,“我们在存在论上用现身情态这个名称所指的东西,在存在者层次上乃是最熟知和最日常的东西:情绪;有情绪。”但他说这种情感是“在存在者层次上”来讲的,实际上就是指的“此在”(Dasein)这样的存在者,这就不是我们所讲的“前存在者”的本源情感——生活情感。
3.建构(construction)。解构及还原并不是哲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终究在于建构,即构造出一个关于存在及存在者的观念系统。其实,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本身也是一套观念系统的建构。下文紧接着要谈的“生活儒学”及其“生活现象学”,也是一种关于存在及存在者的观念系统的建构。对于教育现象学来说,“建构”就是构造出一个关于教育现象的观念系统。
(二)生活现象学的观念
笔者提出的“生活现象学”(Life Phenomenology),作为一种“中国现象学”及“儒学现象学”,乃是生活儒学的现象学维度的集中展示。

黄玉顺:《黄玉顺生活儒学研究》
“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是儒家思想系统的一种当代重建。对于生活儒学来说,“事情本身”既非先验意识的“意向性”,亦非“此在的生存”,而是“生活”。孟子说“民非水火不生活”,其实不仅“民”,“一切的一切都源于生活而归于生活、出于生活而入于生活”。因此,生活儒学最基本的命题是“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但此“存在”(Being)并不等于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概念,而是一个“前存在者”“前主体性”观念,因为“生活”并不以包括“此在”在内的任何存在者为前提。生活儒学认为,唯有以这样的“生活”观念为“大本大源”,才能重建存在者化的形上学、形下学。
这样的“生活”观念即生活现象学的“生活”观念。生活现象学将“生活”视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即“生活现象”。生活现象学的方法同样包含“解构→还原→建构”三大步骤,它的独特性在于其“还原”所通达的“事情本身”就是作为存在的“生活”,而非海德格尔所讲的此在的“生存”(Existenz)。
这里还需注意:绝不能将生活儒学的“生活”混同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有学者的教育哲学专著《回归智慧,回归生活》,其“生活”即实指“生活世界”。笔者曾对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提出质疑,认为“生活儒学所要回归的,乃是非先验性的、前主体性的本源情境,亦即生活本身。而此所谓生活本身,也不是胡塞尔所谓‘生活世界’,因为依照胡塞尔先验论的进路,‘生活世界’观念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困境:假如它是经验的现实,那么它就是首先应该被‘悬搁’的‘超越物’(Transzendenz);而假如它就是纯粹意识本身,那么它就是无关乎现实生活的麻木不仁的东西,因为根据胡塞尔所承认的‘认识论困境’,这样的内在的‘生活世界’是不可能‘切中’外在的现实世界的”。有学者说:“现象学者必须排斥自然科学对自在世界的‘客观’解释,回溯到前科学的‘主观’经验世界,即‘生活世界’之上。”可见,“生活世界”作为“‘主观’经验世界”,就是一个先验概念。而笔者所强调的“复归生活”,绝非回到这样的先验世界。
类似上引“前科学的”表述,有学者说:“现象学对文化和理智生活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确认前哲学的生活、经验和思维的有效性。”这里“前哲学的生活、经验和思维”的表述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仅“思维”不是前哲学的,而且“经验”也未必是前哲学的,例如经验主义哲学的“经验”就不是前哲学的(详上)。不过,其“生活”和“前哲学”概念值得注意。在生活现象学看来,“前哲学”(pre-philosophical)意味着“前主体性”“前存在者”,因为(传统意义的)“哲学”就是“主体性的事情”,也就是存在者的事情;而真正“前哲学”的事情则是“生活”的事情。
二、“成人”:教育现象学的宗旨
教育现象学是一种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学(pedagogy)〔包括现今的“现象学教育学”(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乃是在哲学层面上对教育以及教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一种表现,是教育学界出现的“教育现象学”研究。“教育现象学的视角下,反思是教育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今天,“教育哲学只有首先作为现象学,才能把握住自己”,因此,“教育现象学在中国教育领域正逐渐成为一种‘现象’”。
但是,目前的教育现象学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类本质上截然不同的现象学,即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学。两者尽管都是“现象学”,但实际上分属哲学史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胡塞尔的先验意识的“意向性”仍属传统哲学的某种“存在者”,而海德格尔的“生存”却指向前存在者的“存在”(Sein)。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意义”,是要以“存在”为“存在者”奠基。笔者认为,这是划时代的“存在论转向”(the turn of Being theory),即从传统的“本体论”(ontology)转变为真正意义的“存在论”(the theory of Being),亦即从思考“存在者”转变为思考“存在”(Being),以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这里的转折点无疑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存在论区分”

,即严格区分“存在”(Sein/Being)与“存在者”〔das Seiende(s)/the being(s)〕。因此,笔者的主张不是有学者说的“回到胡塞尔的本义”,而是更多地关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
不过,生活儒学所还原的并非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而是前主体性的生活“情境”(situation)。有学者说:“教育是具体情境中发生着的现象,要理解情境化的教育意义就应注重教育现场,注重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著名教育现象学家范梅南(Max van Manen)说,现象学是“对嵌入在这个情境中的一个典型意识节点的分析、阐释和说明”。这里的“情境”接近于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但“意识”却接近于胡塞尔的先验意识。然而,“生活儒学所要回归的,乃是非先验性的、前主体性的本源情境”;“‘情境’先于‘主体’,而非相反(这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的不彻底性)”。
(一)“生活即教育”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并不彻底,因为他所诉诸的事实上不是“存在”,而是“此在”(Dasein),但是,“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他甚至说“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这就背离了其“存在论区分”的初衷。然而,在生活现象学这里,作为“存在”的“生活”并非“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前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
教育作为一种活动,即属于这样的存在。换言之,教育活动是生活的一种样态,诚如陶行知所言,“学校以生活为中心。一天之内,从早到晚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人之身,从心到手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要之,“教育现象”是一种“生活现象”。本来,“生活”乃是前存在者的,因而浑然无所分别的“存在”观念,可谓“浑沌”;但当我们反思生活的时候,生活就被对象化了,即被存在者化了,于是就有了分别,诸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在这种“分类”的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一种生活”。
进一步说,不仅“教育是一种生活”,而且任何生活样态都可以被视为教育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将这种教育思想表述为“Life education means an education of life,by life and for life”。
教育何为?通俗地说,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即“人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人”是一种存在者,即主体性存在者。因此,教育的宗旨所涉及的就是“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按生活现象学的观念,一切存在者无不源于存在而归于存在,任何主体都源于生活而归于生活;存在给出了存在者,生活给出了主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活就是教育。
不过,“生活即教育”这个命题并非笔者的发明,而是陶行知的思想:他把自己的教育哲学概括为“生活教育”,其核心命题就是“生活即教育”。但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即不是现象学的进路。近年来,有学者尝试“继承与发展”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提出“‘生活·实践’教育”,因为“人的本质是生成的而非预成的,是在‘生活·实践’中生成的,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但同时其也指出,教育现象学并非“实践现象学”,而是“理论现象学”,“是一个理论研究工作者对于实践层面危机拯救的理论担当”。确实,教育现象学是对教育实践的一种理论反思。不过,所谓“实践”其实也是“生活”。因此,无论如何,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这个命题值得我们加以生活现象学的阐释。
(二)教育即“成人”
教育现象学的宗旨,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说,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成人”。所谓“成人”(becoming a human being),就是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to make a person truly human)。如果说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教育哲学及教育现象学的核心问题就是“成人”的问题。
孔子谈到两种含义的“成人”概念,涉及我们这里讨论的“成人”的两个层次。
1.人禽之辨。这是儒家强调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孟子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点点区别,在于人有先天的人性:“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但常人往往遮蔽其本性,所以需要教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这是颇有道理的,人类天生具有人之为人的关乎“人伦”的本性,类似于计算机的“初始化设置”,但并非已经实然地具有“人伦”,所以需要教育。固然,从出生开始,任何人就已经是一个人;但那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所以需要“社会化”(socialization)。
这就是“成人”的问题。“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这里的“成人”似乎并非我们这里讨论的“成人”概念,而是一个名词,而且是谈某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但是,名词的“成人”却是动词“成人”的结果。这里的“文之以礼乐”其实并非多么崇高的境界,而是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具备的社会规范方面的基本素养。朱熹解释:“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在儒家话语中,“礼”是一个泛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安排)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成人”不过是说成为一个认同并且遵守伦理规范的人,谈不上“君子”或“圣人”,就是常人而已。
2.成人之美。“成人”不仅涉及人和动物的差异,而且涉及人与人之间在道德素养上的差异。在儒家话语中,有道德缺陷的人,谓之“小人”。“小人”并非毫无伦理,却有道德缺陷。孔子说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里的“美”意指道德上的“善”。邢昺解释:“此章言君子之于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复仁恕,故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也。”朱熹解释:“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恶之异。”其实,不仅“小人”,现实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说在道德上已经十全十美。“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显然,“成人之美”讲的是使人在道德上变得更好。这无疑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如此,“社会化”当然以“社会”为前提;然而社会及其制度规范并非一成不变的,总是在发展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成人”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者,而是开放性的存在者;也就是说,“人”是可能性的存在者。
那么,怎样“成人”?在现象学存在论的意义上,这就是“主体性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在生活现象学视域下的教育现象学意义上,这就是“教育何以可能”的问题。
三、“在生活”:他者教育
生活儒学的教育现象学分析,需要生活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即“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生活的本源结构”旨在解释包括教育活动在内的所有一切人类活动:“在生活”(existing in life)意谓生活生成主体,“去生活”(going to live)意谓这个主体选择自己的生活(此时的“生活”已非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作为存在的生活)。
所谓“在生活”是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已然置身于某种生活情境之中,并在这种生活情境之中形成或改变自己的主体性;这种情境未必是这个主体的既有主体性的选择,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被抛”(Geworfenheit/thrown)或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谓“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或者即便是这个主体的自觉选择,这个主体也未必能够真正主宰这种情境的趋向,反倒为这种趋向所重塑。无论如何,主体都是“被给与者”(the given being),即被存在或生活所给出的存在者。
显而易见,在教育现象中,无论受教者还是施教者,都是“被给与者”。按照孟子的说法,“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但不仅后知者,而且先知者本身,都是“在生活”中被给出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教育总是“他者教育”(the education of others)。何谓“他者”(the other)?“‘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当然,西方现代哲学的“他者”往往是指主体之外、为主体所塑造的弱者一方。例如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说:“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这样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G.W.F.Hegel),他说:“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但“实际上,‘他者’意识的存在是古今中外的普遍事实,正如‘自我’意识的普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他者’泛指‘自我’以外的一切存在者”。对于教育来说,施教者与受教者互为他者。
“他者教育”包括:施教者方面的“对他者教育”(the education for others);受教者方面的“受他者教育”(the education by others)。
(一)受教者的“在生活”
人首先是被给与者,即“在生活”之中生成的存在者。在教育现象中,人首先是受教者(tutee/the educated one),其主体性首先是被他者给与的。诚如拉康(Jaques Lacan)所说,“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笔者也曾谈到,“我们一开始就是被他者规定的。我记得我在关于‘他者意识’的那篇文章里面专门分析了汉语的‘我’这个字,证明:自我意识的诞生,恰好是由他者规定的。”这里,家长、教师,乃至整个社会,这些“他者”构成了受教者的“在生活”背景。
这里最重要的是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即儒家所说的“礼”,亦即前引孟子所说的“教以人伦”。一般来说,教育的内容不外两大方面,即自然知识与社会伦理。然而,不仅儒家对前者不太感兴趣,更关注“礼”或“人伦”,而且教育哲学或教育现象学作为“人学”,理当以后者为圭臬。不仅如此,事实上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自然知识,知识本质上是主体的一种观念建构。如王阳明所说“意之所在便是物”,即首先取决于主体的意向。况且对于教育来说,选择何种自然知识加以传授,这也是施教者的主体意志。
他者塑造了受教者的主体性,这是价值中性的现象,既可能有正面价值效应,亦可能有负面价值效应。从负面看,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了“权力和知识的合谋在话语中预设了主体”,他指出“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这当然同样适用于教育现象,因而值得警惕。但是,受教者的“在生活”也可能导向正面价值,否则人类历史上就只存在“小人”和“坏人”了。“在生活”之所以是价值中性的,是因为这是“前主体性”的存在,而“善恶”则是主体的判断。
(二)施教者的“在生活”
问界M9的增程设计在此次亚欧自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只需添加95号汽油,即可继续前行,避免了在中亚地区难以找到充电桩的尴尬。
山西藏着个煤老板低调下场造车15年,只不过造乘用车的想法才让这家并不广为人知的“成功”汽车走到台前。
受教者的他者,就是施教者(educator/the educating one)。通常的教育观念,认为教育就是施教者教导受教者。前引孟子所说的“先知先觉者”“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这样一种他者教育。问题在于:施教者本身的主体性又是何以可能的?这仍然是存在论现象学的发问:存在者何以可能?主体性何以可能?对此,可给以三个层次的阐明:
其一,施教者曾经也是受教者,即也是“在生活”的产物。
其二,从狭义的教育活动看,施教者也会受到受教者的反馈影响。这种教育反馈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因材施教”,施教者根据受教者的实际情况而进行自我调整和改变,实质上可以视为受教者对施教者的一种教育,此时受教者即成为了施教者的“在生活”背景。《论语》中有一个典型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对于孔子的两种不同回答,公西华感到困惑,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二是“教学相长”,施教者在教育活动中直接受到受教者的某种教育,此时受教者转变为了施教者的“在生活”背景。《论语》记载了孔子如何受学生影响而自我改变的几个例子:(1)子夏将《诗经》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诠释为“礼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即承认子夏对自己的启发(朱熹解释“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2)曾点说自己的志向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感叹“吾与点也”,欣然接受了曾点的境界;(3)在评论子桑伯子的时候,冉雍表达了与孔子不同的看法,孔子承认“雍之言然”;(4)“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言偃也表达了与孔子不同的看法,孔子承认“偃之言是也”。这样的教学,笔者称之为“前主体性对话”。唯其如此,孔子才会感叹:“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其三,从广义的教育活动看,施教者同时也始终是受教者,因为施教者始终依然“在生活”。
四、“去生活”:自我教育
所谓“去生活”是指,当一个主体由“在生活”给定之后,这个主体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其主体性,即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去生活”意味着主体的可能性的敞开。对于教育现象来说,如果说“生活即教育”,那么,显而易见,一个主体的“去生活”即这个主体的“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如果说任何主体必然“去生活”,那么,任何教育归根到底都是自我教育。
(一)“去生活”与主体选择
主体的自我教育,出自主体的自我选择。例如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里的“我欲仁”就是孔子的一种“去生活”。为此,孔子作出了交友方面的选择,即“亲仁”,亦即“有仁德者则亲而友之”,“友其士之仁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他还作出了生活环境方面的选择:“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这是一种理智的选择:“未知(智),焉得仁?”相传“孟母三迁”“择邻而居”,也是同样的道理。古人“卜邻”也是一种择邻,晏婴说“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杜预注:“卜良邻。”今天的“择校”,也是某种意义的自我教育。
当然,“我欲仁”未必就“斯仁至矣”,未必就能“欲仁而得仁”“求仁而得仁”,因为“去生活”其实终究仍然还是“在生活”。如上文谈到过的,主体未必总是能够掌控当下生活情境的趋向;然而无论如何,主体性意味着选择性,意味着主体的自我教育。
那么,“欲仁”的这个“我”、这个主体何来?这就要回到“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前引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表明,“欲仁”的选择涉及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要求。确实,一个人的社会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受、遵守这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否则,这个人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因此,孔子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就是说,社会规范,即“礼”,给与了“欲仁”的动机;这其实就是“在生活”给与了主体的动机。这看起来不再是“自我教育”,而是一种“他者教育”了。这就是说,“去生活”终究归属于生活。
此外,必须指出,“克己复礼”只是孔子礼学思想的一个层面,如果仅限于此,就可能成为“小人儒”,成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乡原”。因为,并非任何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都是正义的,除非它们不仅符合“正当性原则”,即真正出自仁爱的动机;而且即便曾经正义的制度规范也未必仍然是正义的,除非它们符合“适宜性原则”,即具有适应一个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效果。因此,孔子礼学思想中更深刻的层面乃是“礼”有“损益”,即儒家的社会正义论。
这是更深刻的“我欲仁”。所谓“仁”,首先是一种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不仅如此,这种情感并非所谓“性之所发”的主体情感,而是前主体性的情感,因为正是这种情感给出了“仁者”这样的主体。为此,对于儒家来说,首要的不是哲学,而是诗学,孔子指出:“兴于诗,立于礼。”这就是说,仁者的主体性是在“学诗”中“兴起”的(朱熹解释“兴,起也”;“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这是因为真正的诗是本真情感的表达,“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由此可见,最本真的教育是“情感教育”(emotional education),尤其是“爱的教育”,“礼教不如诗教,道德教育不如情感教育”,“孔子之重诗教,首先重在情教,这是孔子‘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的自然体现”。
(二)“去生活”与教育自由
主体的选择乃是自由意志的表现;主体“去生活”的“我欲仁”也是自由意志的表现。“‘自由’指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这里首要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这种意志乃是主体性的根本特征,它并非所谓“实践理性”的一个“公设”(postulate),而是“在生活”所给与的人格内涵。
对于教育来说,这里涉及的就是“教育自由”(freedom of education)的问题。狭义的教育自由,指主体选择教育内容及其形式的自由。这里属于广义的教育自由,就是说,如果“生活即教育”,那么,教育自由就是主体“去生活”的自由。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这种“自得”其实不限于“君子”,而是任何人“去生活”的必然。
由于这种自由出自主体意志的自主选择,因此,教育自由的本质就是主体在“去生活”之中的自我教育。但是,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否成为实践中的意志自由,即能否真正实现教育自由,这还要取决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条件。这就涉及“教育权”(the right of education)问题。教育权通常被片面地理解为“受教育权”(the right to education),其实,教育权的本质是“自我教育权”(the right of self-education),即主体“去生活”的自由权利。
